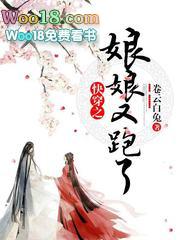笔看阁>重生后我要当富婆 > 绣花发展(第1页)
绣花发展(第1页)
正月十六这天,李家村育红班正式开班。
二十多个娃娃挤在刷了石灰水的屋子里,小脸仰得老高。赵小田穿着压箱底的的确良衬衫,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:"春"。
最让人意外的是李三木——他不知从哪弄来架旧风琴,往墙角一摆,"我媳妇当年在宣传队弹过这个。。。"
琴声响起时,张翠翠看见赵小田抹了把眼角。
窗外,篷布招牌在春风里轻轻晃动,"利民综合服务社"几个大字下,不知谁添了行歪歪扭扭的小字:"兼育红班报名处"。
傍晚盘账时,张翠翠发现个有趣的现象:今天卖得最好的不是油盐酱醋,而是铅笔和橡皮。
五爷爷蹲在门槛上笑,"我家那小子,非要买带熊猫的文具盒,说是明天给赵老师看。"
一个月后,育红班的名声传到了镇上,妇联主任都来看这个育红班。
-瑛子领着小伙伴们唱"小燕子";
-四妹虽然不会说话,却能用剪纸教形状;
-最绝的是李梅设计的"识字围裙"——每个口袋绣着不同偏旁,孩子们拼对了就给块水果糖。
记者刚走,供销社的王主任就上门了,"翠翠,你这育红班。。。能不能兼着代销文具?"
清明前后,杂货铺门口多了块新牌子:"李家村育红用品专供"。赵寡妇带着老太太们缝制布书包,一个能赚八毛钱;李梅设计的"算术口袋"被县教育局批量订购;连五爷爷都重操旧业,做起了木制拼图。
最让人惊喜的是孩子们的变化。铁蛋家小子从前见人就躲,现在能大大方方站在黑板前算账:"俺爹买化肥,一百斤九块八,二百斤就是。。。就是。。。"
"十九块六!"满屋子的娃娃齐声喊道,清脆的声音惊飞了屋檐下的燕子。
夕阳西下,张翠翠坐在门槛上数着今天的收入——育红班收费每人每月两块,但卖文具和手工品的利润倒有十五六块。她望着远处绿油油的麦田,突然想起赵寡妇那句话:
"机器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"
如今这小小的育红班,不正是给全村播下了最鲜活的种子?
要说卖的最好的,还得是衣服。
这不,杂货铺开张那天,李梅运来了第一批机器制作的成衣。十件的确良衬衫,领子挺括得像糊了浆,袖口的扣眼大小分毫不差。
"这。。。"村里的姑娘们摸着衣服直咂嘴,"比县百货大楼的还板正!"
王婶却撇撇嘴,"没魂儿!你看这扣子周边,连个回针都没有,穿三个月准开线。"
李梅不慌不忙翻开衣领内侧——那里用黄线绣了朵小小的茉莉,正是赵寡妇亲传的"藏针"技法。"机器活是卖给讲究人的,咱这暗功夫是留给识货的。"
当晚,赵寡妇把李梅叫到里屋。老太太抖开件手工缝制的对襟褂,领口绣着繁复的"卍"字纹。
"丫头,知道这花纹费了多少工吗?"烟袋锅点着纹样,"整整七天!现在机器一刻钟就能仿个八成。。。"
李梅摸出块碎布头,上面用机器绣了简化版的"卍"字,虽然少了些灵动,但远看几乎乱真。
"师傅,农机站的工人们说。。。他们等不起七天。"
油灯"噼啪"爆了个灯花。赵寡妇盯着那块布看了许久,突然起身从箱底翻出本账册:"1958年,公社让我三天赶五十面红旗。。。手指头磨出血也没做完,"她枯瘦的手指抚过缝纫机,"这铁家伙,是来救命的。"